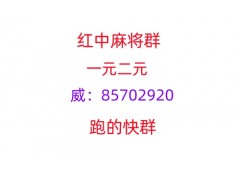請將你關切的注視做我今生漂泊的拐杖吧,讓一段情緣溫暖我孤寂的心憔悴的面容,讓我不再在歲月的篇章中啜泣,不再在啜泣中流浪
記得小時候故鄉唱社戲,父母親及祖父祖母總會早早地做完午飯或晚飯,然后拿著小板凳去戲場占個好位置,一邊和身旁或生或熟的人們拉家常,又時不時抬頭向戲臺上張望幾眼
當一串大紅的鞭炮吼上一通之后,眾鄉親們總會像得到命令一般坐正身子,停止交談,聚精會神地融入到角色之中!動情之處總會有老人淚濕衣襟,甚至低聲抽泣
而像我這種懵懂世事的孩子,最怕被父母親抱在懷里看那些像穿壽衣一樣的人在臺子上轉來轉去,口里咿咿呀呀的,一句唱詞半天唱不完,憋得人難受
所以,總會在此時悄悄溜出戲場,去看場電影或買把水和朋友們打水仗樂去了!回到家偶爾大人會問,今天演得啥戲呀,便吱唔搪塞一陣,大人自不追究,高興時,還會撫著孩兒的頭,講起戲中的故事,講得很認真、很動情
2、散文語言的炫技性愈演愈烈,它對于散文的內核和干凈會存在傷害嗎?你怎樣避免語言的炫技性對散文本身的傷害? 3、一直佩服楊兄的散文評論文字,請問你在實際創作中怎樣把握散文的情感結構和精神結構? 答樊健軍問:散文同化問題有兩個方面的原因,一個是現代傳媒造成的,比如說文學論壇,時常存在這樣的一個現象,阿貝爾的《1976,青苔或水葵》寫的好,一下子就會冒出許多類似題材的作品,這也就是說,大家的跟風心理是嚴重的,從而導致了散文寫作題材的同化;二是思維和生活面的日益狹窄
很多的作家,一旦寫到了某種程度,就有些思維僵化了,一條路走到黑,從不認真審視和自覺校正自己的寫作
黃海說得好,同一位作家,一篇作品與另一篇作品大相徑庭,風牛馬不相及,那么他的寫作肯定還會有生長點的,另外,我們的一些寫作者,之所以能夠很好地坐下來寫東西,背后唯一的支撐是他擁有了今日不為明日憂的物質基礎
這是好事,但也是壞事,國人的問題是,自家吃飽穿暖了,很少再去關注他人,心的窄導致了生活面的窄,久而久之,似乎就沒有什么可寫了,除了已有的生活經驗和內心情感,便很難在題材和思維上有所突破
論壇同化,我想大抵是三個方面的原因,一個是主張和喜好迥然有別,不同而不容;二是個人問題,我總是覺得,論壇非個人所有,斑竹只是管理者和服務者,而不是所有者,要做論壇,首先要明白這個因果關系,把論壇當作自家的一畝三分地,那肯定是狹隘的
三是論壇必須要走合并或者聯盟之路,集腋成裘,沙中淘金,才能做的更好,才能為更多的參與者服務
避免個人被同化是一個涉及到個人寫作前途的問題,我覺得,每一個寫作者都應當具備一種自覺的分析和認知能力,要透過迷霧看到本質,要站在整個寫作態勢的高度上,去度量和取舍,既要堅守自己的文學理念,也要隨時調整和充實自己的寫作思想
一句話,既要安裝反間諜程式,又要時常更新病毒碼
關于炫技問題,上面已有所回答,首先要肯定,炫技是一種富有才華的表現,這種行為大抵是存在于那些初出茅廬的年輕寫作者身上,我相信,到40歲以后,再回身來看,對自己當時的炫技表演就會有點不好意思的
樸素大美,這是先賢們百說不厭的一個常識性問題
返璞歸真、行云流水、肯定是我們必然要回歸的終點
我自己好像也存在上面三個炫技的嫌疑,如何避免,我想隨著年齡的增長,會有所改觀的
我的文學批評不足道哉,純粹是興之所至,信口開河,指鹿為馬,與嚴肅的批評家比起來,小巫都算不上
還是那句話,我有我的一種評判作品的標準和方法,那就是它們到底是個什么樣子,包括作者的寫作態度,對事物的認知水準,書寫方式等,因為從一個人的文字里面,大致可以得知這個人的心性,雖然有人格分裂、二律被反的現象,但說起來,仍舊是少數的,另外,我也相信,每個寫作者都是善良的,至于那些蠅營狗茍,精于算計,城府猶如地獄的寫作者,我敢說,他們的尾巴并不會比兔子長多少
甘肅?鐵翎問:中國當下的文學創作,“寫什么”和“怎么寫”是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
我想問的是:在你們的寫作生涯中,你所面臨的寫作“瓶頸”是什么?是怎樣處理的?或者說,是怎樣克服的? 答甘肅?鐵翎問:鐵翎兄好,感謝你的問題
首先要聲明的是,作為一個業余寫作者,我始終是邊緣的,身體的偏乃至文學的偏,不像其他朋友,有地理近的和情感的近,可以很快地靠近文學主流(起碼是媒體主流)
我至今悲哀的是:在文學上,國外除外,在國內沒有一個真正讓我佩服的偶像,這是很糟糕的,也是極其幸運的,我不迷信任何一個人,哪怕他身居高職,掌握傳播大權
也不瞞你說,我曾經有過此類想法,也曾付出行動,但很快,我就覺得了那種事情無意義乃至和個人內心的某種不協調
以此來回答你的問題,我覺得要容易的多,也就是說,“寫什么”這問題完全在于個人,對于一個作家,寫自己熟悉的,掌握和了解透徹的,爛熟于心的,才能夠寫的好,寫的到位
“怎么寫”是一個方法論,條條大路通羅馬,放在文學的怎么寫依舊有效
關于這個問題,只要是適合,能夠真正接近于你所需要抵達的目的方式,都可以拿來使用,但有兩個原則,一是選擇最容易貼近的,而是要有所創新,不能跟著他人跑
關于第二個問題,“瓶頸”應當是個經濟學術語吧,我也拿一個武俠小說的話來作回應
那就是“任督二脈”,金庸的書中常說,只要打通了任督二脈,才可以獲得上乘武功
在文學這個路上,好多人半途而廢(我之所以還在掙扎,是因為還對自己懷有那么一點點期望)
你說的這個問題,就是寫到了某種程度,突然卡殼了,突破不了自己
我的方法或者說經驗是,我絕對不把太熱的作家作品當回事,也不會以文學來祈求文學的突破
這時候,我覺得,我的興趣和眼光,都要向外看,脫離文學,而旁涉其它門類
我不大喜歡閱讀純粹的文學作品,倒是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感興趣
我覺得,文學的洋洋萬言,始終抵不過先哲的只言片語,這是令人沮喪的
說到這里,文學不過是一種文字形式罷了
以非理性來呈現理性之外的某些情緒、客觀事實和個人想象
還要說的是,文學的某些事情不是“處理和克服”這些技術性詞匯可以去掉的! 與山提問:如何才能走向文字的成熟,如何才能走向文字的特色?什么樣的道路才是寫作者從開始到最終的應該要走的路?請楊兄談一下自己的觀點?請問地域是否會對寫作產生影響,比如你的西北風
答與山:這個問題有點大,但也很小
文學創作是一個長期的過程,不是朝夕即可的,起碼不會像流傳的愛情一樣,暮合朝分,一個寫作者,需要的是長期的過程
沈從文說:“寫作沒有什么訣竅,就是多寫……寫多了就寫的好了
”我想先生是說對了的,拿我當初,絕對不如與山先生現在,只要功夫深,鐵杵磨成針,我相信這個道理
這是我的一點看法,我乃愚笨之人,不像那些大家天才,笨功夫下得多一點
文字的特色實際上就是個人的特色,一個人的性情乃至趣味體現,似乎不是單一的,包括了地域、內心、知識、情趣、方法、喜好、道德審美、人人精神等等因素
寫作還是決定于個人的造化,走向成熟從另一方面說,是走向沒落和寂滅
在寫作當中,成熟并不是一個好的詞匯,尤其對于寫作者來說,是致命的
至于什么樣的道路是寫作者應當走的道路,我覺得,一個是堅持,一個是創新,還有一個是自我的不滿
堅持是對自己所理解的文學理念的緊追不舍,是對“本我”乃至夢想的特別肯定;創新是寫作的首要品質,沒有創新,就沒有
以前褒湯的時候總不忍不住把火開大些,為了節省時間,事實上是因為自己沒有耐性
為了湯的滋味更浸些,我只能用最低級的揚湯止沸的方法來延長時間,
被稱為“詩中有畫,畫中有詩”的唐代大畫家王維,他就出生在一個佛教氣氛濃厚的家庭
王維的母親褐衣蔬食,持戒安禪,樂住山林,志求寂靜
王維和他弟弟王縉也信奉佛教,居常蔬食
王維雖有一段從政生活,但因后來失利,從此便名利之心皆無,誠心奉佛,淡泊處世,以詩畫自娛養性
三十歲時,王維喪妻,傷痛欲絕,寫石道:“宿昔朱顏成暮齒,須臾白發變垂髻
一生幾許傷心事,不向空門何處銷
”王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,空門深處可以銷盡人世的七情六欲,讓傷心也變得淡定
《舊唐書》本傳曾記載:王維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
輞水周于舍下,別漲竹洲花塢,與道友泛舟往來,彈琴賦詩,嘯詠終日,嘗聚其田園詩,號《輞川集》,又以此作《輞川圖》
以此可見王維專心宗教的心境和迷戀田園生活的態度
蘇軾題《書摩詰藍田煙雨圖》云:“味摩詰之詩,詩中有畫;觀摩詰之畫,畫中有詩”
以上就是關于人生不相見1-2元紅中麻將親友圈一元一分貼吧/微博全部的內容,關注我們,帶您了解更多相關內容。
特別提示:本信息由相關用戶自行提供,真實性未證實,僅供參考。請謹慎采用,風險自負。